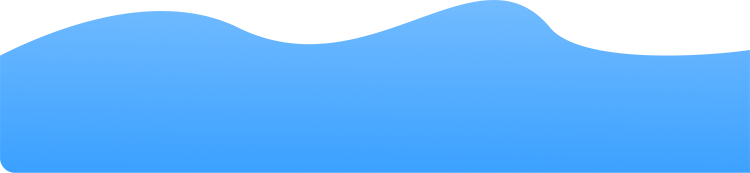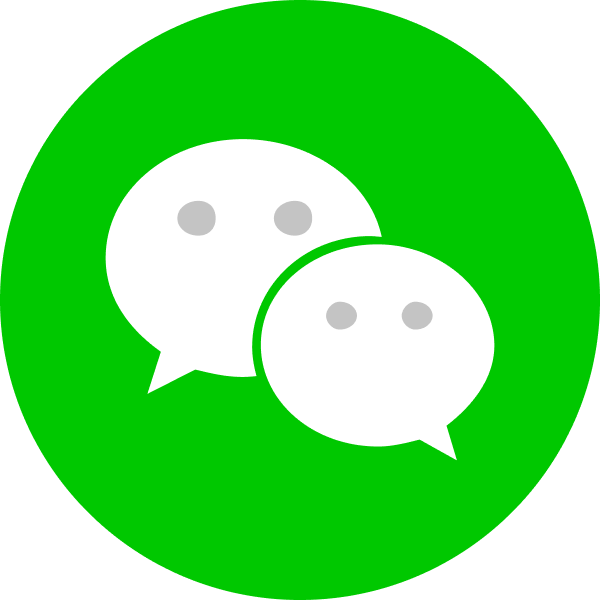相关题目
6、(六)大年初一没下雪 去年三十傍晚,广州火车站突然静下来。时间还早,我买了份报纸,走向车厢。车厢里没人,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 不知到了哪个小站,上来一个农民模样的人,牵着个小女孩,对着车票仔细核对座号,辨认清楚了,他们才坐下。整个车厢其实没几个人,你想坐哪儿都行。一看就知,他们是不常坐车的。 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,灰黄的脸,很深的皱纹。女孩的脸也是灰黄的,土头土脸的样子,他们坐在我对面。男人坐下去时,半哈着腰,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,好像说:打搅了! 这一路肯定无聊透了,你别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在火车上玩牌了,我继续看我的书。晚上,餐车送了一次面条,黏糊糊的,看着都没胃口。我拿出上车前买的江南酱鸭,要了一瓶啤酒,准备凑合着吃一顿年夜饭。 我请对面的一起吃。男人连摆着手,说不吃,不吃。小女孩看着面包,咽了一下口水。我递过去一块面包,又撕了一只大鸭翅,笑着说:“吃吧,都过年了,客气啥!”我又拿出花生米、凤爪几样下酒菜,索性喝个痛快。 我边吃边问:“你们回家过年?”“嗯……不,小孩子没看过雪,带她去看雪。” “喔。”我嘴里应着,心想中国还有这么浪漫的农民。 没怎么说话,饭很快吃完了,酒也喝光了。男人主动收拾桌上的碎骨。小女孩突然问我:“叔叔,你看见过雪吗?”我很舒适地斜倚在椅背上,笑着说:“见过,白的,有的人说像糖,有的人说像盐……” “你给我说说吧,说说吧。”说着话,我想去洗手间,路过洗手池旁的过道,我看见那个男人抱着头,蹲在地上哭泣。 在男人断断续续的哭泣中,我听到那女孩的故事。在她四岁时母亲去世了,九岁时她得了白血病,医生说今年可能是她最后一个春节了。爸爸问她想要啥,她说只想看看雪,生长在广东偏僻的山区,她从来没有见过雪。《济南的冬天》那篇文章激起了她看雪的愿望,在她的脑海中不断想象着真正冬天的模样。这个一贫如洗的父亲在大年三十晚上和她一起坐火车准备看雪。坐着这趟车去,坐着当晚的车回,再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住旅店和车上吃饭了。临走前,他们听了天气预报,说杭州今夜有一场大雪。 我无法想象在这样一张灰黄皮肤的脸庞下有这样一颗细腻的心。 我走到座位旁,给小女孩耐心地讲起下雪时的种种趣事。她那双黑眼睛就像在灰烬里的火星,一闪一闪的……到站了,杭州很冷,风很大,却没有雪。我拿了三百块钱给他,他死活不要。我留了一堆食品给他们。他们送我上了回家的中巴,在车旁拼命地摇着手。 在回乡的时候,最怕碰风雪天,而我希望今天赶快下雪,下得越大越好。 一天无雪,一夜无雪。初三的晚上,一家人坐在火炉旁吃火锅,窗玻璃上响起了淅淅的声音。我突然说了声:“下雪了。”(选自《读者》有改动)3.如果将结尾改为:下车时,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……和本文的结尾比较,哪一个好些?请作简要分析。
6、(六)大年初一没下雪 去年三十傍晚,广州火车站突然静下来。时间还早,我买了份报纸,走向车厢。车厢里没人,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 不知到了哪个小站,上来一个农民模样的人,牵着个小女孩,对着车票仔细核对座号,辨认清楚了,他们才坐下。整个车厢其实没几个人,你想坐哪儿都行。一看就知,他们是不常坐车的。 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,灰黄的脸,很深的皱纹。女孩的脸也是灰黄的,土头土脸的样子,他们坐在我对面。男人坐下去时,半哈着腰,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,好像说:打搅了! 这一路肯定无聊透了,你别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在火车上玩牌了,我继续看我的书。晚上,餐车送了一次面条,黏糊糊的,看着都没胃口。我拿出上车前买的江南酱鸭,要了一瓶啤酒,准备凑合着吃一顿年夜饭。 我请对面的一起吃。男人连摆着手,说不吃,不吃。小女孩看着面包,咽了一下口水。我递过去一块面包,又撕了一只大鸭翅,笑着说:“吃吧,都过年了,客气啥!”我又拿出花生米、凤爪几样下酒菜,索性喝个痛快。 我边吃边问:“你们回家过年?”“嗯……不,小孩子没看过雪,带她去看雪。” “喔。”我嘴里应着,心想中国还有这么浪漫的农民。 没怎么说话,饭很快吃完了,酒也喝光了。男人主动收拾桌上的碎骨。小女孩突然问我:“叔叔,你看见过雪吗?”我很舒适地斜倚在椅背上,笑着说:“见过,白的,有的人说像糖,有的人说像盐……” “你给我说说吧,说说吧。”说着话,我想去洗手间,路过洗手池旁的过道,我看见那个男人抱着头,蹲在地上哭泣。 在男人断断续续的哭泣中,我听到那女孩的故事。在她四岁时母亲去世了,九岁时她得了白血病,医生说今年可能是她最后一个春节了。爸爸问她想要啥,她说只想看看雪,生长在广东偏僻的山区,她从来没有见过雪。《济南的冬天》那篇文章激起了她看雪的愿望,在她的脑海中不断想象着真正冬天的模样。这个一贫如洗的父亲在大年三十晚上和她一起坐火车准备看雪。坐着这趟车去,坐着当晚的车回,再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住旅店和车上吃饭了。临走前,他们听了天气预报,说杭州今夜有一场大雪。 我无法想象在这样一张灰黄皮肤的脸庞下有这样一颗细腻的心。 我走到座位旁,给小女孩耐心地讲起下雪时的种种趣事。她那双黑眼睛就像在灰烬里的火星,一闪一闪的……到站了,杭州很冷,风很大,却没有雪。我拿了三百块钱给他,他死活不要。我留了一堆食品给他们。他们送我上了回家的中巴,在车旁拼命地摇着手。 在回乡的时候,最怕碰风雪天,而我希望今天赶快下雪,下得越大越好。 一天无雪,一夜无雪。初三的晚上,一家人坐在火炉旁吃火锅,窗玻璃上响起了淅淅的声音。我突然说了声:“下雪了。”(选自《读者》有改动)2.对小说理解赏析不正确的一面是( )
6、(六)大年初一没下雪 去年三十傍晚,广州火车站突然静下来。时间还早,我买了份报纸,走向车厢。车厢里没人,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 不知到了哪个小站,上来一个农民模样的人,牵着个小女孩,对着车票仔细核对座号,辨认清楚了,他们才坐下。整个车厢其实没几个人,你想坐哪儿都行。一看就知,他们是不常坐车的。 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,灰黄的脸,很深的皱纹。女孩的脸也是灰黄的,土头土脸的样子,他们坐在我对面。男人坐下去时,半哈着腰,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,好像说:打搅了! 这一路肯定无聊透了,你别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在火车上玩牌了,我继续看我的书。晚上,餐车送了一次面条,黏糊糊的,看着都没胃口。我拿出上车前买的江南酱鸭,要了一瓶啤酒,准备凑合着吃一顿年夜饭。 我请对面的一起吃。男人连摆着手,说不吃,不吃。小女孩看着面包,咽了一下口水。我递过去一块面包,又撕了一只大鸭翅,笑着说:“吃吧,都过年了,客气啥!”我又拿出花生米、凤爪几样下酒菜,索性喝个痛快。 我边吃边问:“你们回家过年?”“嗯……不,小孩子没看过雪,带她去看雪。” “喔。”我嘴里应着,心想中国还有这么浪漫的农民。 没怎么说话,饭很快吃完了,酒也喝光了。男人主动收拾桌上的碎骨。小女孩突然问我:“叔叔,你看见过雪吗?”我很舒适地斜倚在椅背上,笑着说:“见过,白的,有的人说像糖,有的人说像盐……” “你给我说说吧,说说吧。”说着话,我想去洗手间,路过洗手池旁的过道,我看见那个男人抱着头,蹲在地上哭泣。 在男人断断续续的哭泣中,我听到那女孩的故事。在她四岁时母亲去世了,九岁时她得了白血病,医生说今年可能是她最后一个春节了。爸爸问她想要啥,她说只想看看雪,生长在广东偏僻的山区,她从来没有见过雪。《济南的冬天》那篇文章激起了她看雪的愿望,在她的脑海中不断想象着真正冬天的模样。这个一贫如洗的父亲在大年三十晚上和她一起坐火车准备看雪。坐着这趟车去,坐着当晚的车回,再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住旅店和车上吃饭了。临走前,他们听了天气预报,说杭州今夜有一场大雪。 我无法想象在这样一张灰黄皮肤的脸庞下有这样一颗细腻的心。 我走到座位旁,给小女孩耐心地讲起下雪时的种种趣事。她那双黑眼睛就像在灰烬里的火星,一闪一闪的……到站了,杭州很冷,风很大,却没有雪。我拿了三百块钱给他,他死活不要。我留了一堆食品给他们。他们送我上了回家的中巴,在车旁拼命地摇着手。 在回乡的时候,最怕碰风雪天,而我希望今天赶快下雪,下得越大越好。 一天无雪,一夜无雪。初三的晚上,一家人坐在火炉旁吃火锅,窗玻璃上响起了淅淅的声音。我突然说了声:“下雪了。”(选自《读者》有改动)1.“我”对父女俩的情感有什么变化?
5、(五)雨不但可嗅,可亲,更可以听。听听那冷雨。听雨,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,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。大陆上的秋天,无论是疏雨滴梧桐,或是骤雨打荷叶,听去总有一点凄凉,( ),( ),于今在岛上回味,则在凄楚之外,再笼上一层( )了。雨打在树上和瓦上,韵律都清脆可听。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,(那古老的音乐,属于中国)。王禹偁在黄冈,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。据说住在竹楼上面,急雨声如瀑布,密雪声比碎玉,而无论鼓琴,咏诗,下棋,投壶,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。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,任何细脆的声响,怕都会加倍夸大,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。雨天的屋瓦,浮漾湿湿的流光,灰而温柔,迎光则微明,背光则幽黯,对于视觉,是-种低沉的安慰。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,由远而近,轻轻重重轻轻,夹着-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,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,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。“下雨了。”温柔的灰美人来了,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,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。 ——选自余光中《听听那冷雨》4.从修辞角度赏析选文第3段划线句,不超过50字。
5、(五)雨不但可嗅,可亲,更可以听。听听那冷雨。听雨,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,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。大陆上的秋天,无论是疏雨滴梧桐,或是骤雨打荷叶,听去总有一点凄凉,( ),( ),于今在岛上回味,则在凄楚之外,再笼上一层( )了。雨打在树上和瓦上,韵律都清脆可听。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,(那古老的音乐,属于中国)。王禹偁在黄冈,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。据说住在竹楼上面,急雨声如瀑布,密雪声比碎玉,而无论鼓琴,咏诗,下棋,投壶,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。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,任何细脆的声响,怕都会加倍夸大,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。雨天的屋瓦,浮漾湿湿的流光,灰而温柔,迎光则微明,背光则幽黯,对于视觉,是-种低沉的安慰。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,由远而近,轻轻重重轻轻,夹着-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,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,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。“下雨了。”温柔的灰美人来了,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,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。 ——选自余光中《听听那冷雨》3.第2段联想王禹偁《黄冈竹楼记》,对其作用的分析,错误的一项是( )
5、(五)雨不但可嗅,可亲,更可以听。听听那冷雨。听雨,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,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。大陆上的秋天,无论是疏雨滴梧桐,或是骤雨打荷叶,听去总有一点凄凉,( ),( ),于今在岛上回味,则在凄楚之外,再笼上一层( )了。雨打在树上和瓦上,韵律都清脆可听。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,(那古老的音乐,属于中国)。王禹偁在黄冈,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。据说住在竹楼上面,急雨声如瀑布,密雪声比碎玉,而无论鼓琴,咏诗,下棋,投壶,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。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,任何细脆的声响,怕都会加倍夸大,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。雨天的屋瓦,浮漾湿湿的流光,灰而温柔,迎光则微明,背光则幽黯,对于视觉,是-种低沉的安慰。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,由远而近,轻轻重重轻轻,夹着-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,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,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。“下雨了。”温柔的灰美人来了,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,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。 ——选自余光中《听听那冷雨》2.第2段画线句“那古老的音乐,属于中国”含义的理解,最准确的一项是( )
5、(五)雨不但可嗅,可亲,更可以听。听听那冷雨。听雨,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,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。大陆上的秋天,无论是疏雨滴梧桐,或是骤雨打荷叶,听去总有一点凄凉,( ),( ),于今在岛上回味,则在凄楚之外,再笼上一层( )了。雨打在树上和瓦上,韵律都清脆可听。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,(那古老的音乐,属于中国)。王禹偁在黄冈,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。据说住在竹楼上面,急雨声如瀑布,密雪声比碎玉,而无论鼓琴,咏诗,下棋,投壶,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。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,任何细脆的声响,怕都会加倍夸大,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。雨天的屋瓦,浮漾湿湿的流光,灰而温柔,迎光则微明,背光则幽黯,对于视觉,是-种低沉的安慰。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,由远而近,轻轻重重轻轻,夹着-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,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,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。“下雨了。”温柔的灰美人来了,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,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。 ——选自余光中《听听那冷雨》1.在选文第1段空格里填入一组词语,最准确的一项是( )
4、(四)阳关雪余秋雨我曾有缘,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,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,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。我的周围,人头济济,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,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。人们来寻景,更来寻诗。有时候,这种焦渴,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,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。文人的魔力,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,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。他们褪色的青衫里,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?今天,我冲着王维的那首《渭城曲》,去寻阳关了。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,回答是:“路又远,也没什么好看的,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。” 老者抬头看天,又说:“这雪一时下不停,别去受这个苦了。”我向他鞠了一躬,转身钻进雪里。一走出小小的县城,便是沙漠。除了茫茫一片雪白,什么也没有,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。在别地赶路,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,盯着一棵树,赶过去,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,赶过去。在这里,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,哪怕是一片枯叶,一个黑点。于是,只好抬起头来看天。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,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,边沿全是挺展展的,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。有这样的地,天才叫天。有这样的天,地才叫地。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,侏儒也变成了巨人。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,巨人也变成了侏儒。天竟晴了,风也停了,阳光很好。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,并不动,却在加深,疑惑半晌,才发现,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。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——那全是远年的坟堆,那么多,排列得又那么密,只可能有一种理解:这里是古战场。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,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《荒原》。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:如雨的马蹄,如雷的呐喊,如注的热血。中原慈母的白发,江南春闺的遥望,湖湘稚儿的夜哭。随着一阵烟尘,又一阵烟尘,都飘散远去。我相信,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;我相信,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,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。于是,他们扭曲地倒下了,化作沙堆一座。远处已有树影。急步赶去,树下有水流,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。登上一个坡,猛一抬头,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,我凭直觉确信,这便是阳关了。转几个弯,再直上一道沙坡,爬到土墩底下,四处寻找,近旁正有一碑,上刻“阳关古址”四字。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。西北风浩荡万里,直扑面来,踉跄几步,方才站住。脚是站住了,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。这儿的雪没有化,当然不会化。所谓古址,已经没有什么故迹,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,就是刚才看到的土墩。土墩已坍了大半,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,一层层苇草,苇草飘扬出来,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。眼下是西北的群山,都积着雪,层层叠叠,直伸天际。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。对于这么一个阳关,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,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: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 这杯酒,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,一饮而尽的。这便是唐人风范。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,执袂劝阻。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,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。告别是经常的,步履是放达的。这种风范,在李白、高适、岑参那里,焕发得越加豪迈。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,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,形体那么健美,目光那么平静,神采那么自信。而唐代,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。王维诗画皆称一绝。但是,长安的宫殿,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,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,去制造一点娱乐。阳关的风雪,竟越见凄迷。于是,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。阳关,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。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,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。即便是土墩,是石城,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,阳关坍弛了,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。它终成废墟,终成荒原。身后,沙坟如潮,身前,寒峰如浪。谁也不能想象,这儿,一千多年之前,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,艺术情怀的弘广。回去罢,时间已经不早。怕还要下雪。2.本文选自《文化苦旅》,结合本文内容,回答作者阳关之旅“苦”在何处。
4、(四)阳关雪余秋雨我曾有缘,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,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,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。我的周围,人头济济,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,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。人们来寻景,更来寻诗。有时候,这种焦渴,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,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。文人的魔力,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,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。他们褪色的青衫里,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?今天,我冲着王维的那首《渭城曲》,去寻阳关了。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,回答是:“路又远,也没什么好看的,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。” 老者抬头看天,又说:“这雪一时下不停,别去受这个苦了。”我向他鞠了一躬,转身钻进雪里。一走出小小的县城,便是沙漠。除了茫茫一片雪白,什么也没有,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。在别地赶路,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,盯着一棵树,赶过去,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,赶过去。在这里,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,哪怕是一片枯叶,一个黑点。于是,只好抬起头来看天。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,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,边沿全是挺展展的,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。有这样的地,天才叫天。有这样的天,地才叫地。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,侏儒也变成了巨人。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,巨人也变成了侏儒。天竟晴了,风也停了,阳光很好。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,并不动,却在加深,疑惑半晌,才发现,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。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——那全是远年的坟堆,那么多,排列得又那么密,只可能有一种理解:这里是古战场。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,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《荒原》。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:如雨的马蹄,如雷的呐喊,如注的热血。中原慈母的白发,江南春闺的遥望,湖湘稚儿的夜哭。随着一阵烟尘,又一阵烟尘,都飘散远去。我相信,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;我相信,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,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。于是,他们扭曲地倒下了,化作沙堆一座。远处已有树影。急步赶去,树下有水流,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。登上一个坡,猛一抬头,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,我凭直觉确信,这便是阳关了。转几个弯,再直上一道沙坡,爬到土墩底下,四处寻找,近旁正有一碑,上刻“阳关古址”四字。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。西北风浩荡万里,直扑面来,踉跄几步,方才站住。脚是站住了,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。这儿的雪没有化,当然不会化。所谓古址,已经没有什么故迹,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,就是刚才看到的土墩。土墩已坍了大半,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,一层层苇草,苇草飘扬出来,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。眼下是西北的群山,都积着雪,层层叠叠,直伸天际。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。对于这么一个阳关,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,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: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 这杯酒,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,一饮而尽的。这便是唐人风范。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,执袂劝阻。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,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。告别是经常的,步履是放达的。这种风范,在李白、高适、岑参那里,焕发得越加豪迈。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,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,形体那么健美,目光那么平静,神采那么自信。而唐代,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。王维诗画皆称一绝。但是,长安的宫殿,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,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,去制造一点娱乐。阳关的风雪,竟越见凄迷。于是,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。阳关,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。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,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。即便是土墩,是石城,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,阳关坍弛了,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。它终成废墟,终成荒原。身后,沙坟如潮,身前,寒峰如浪。谁也不能想象,这儿,一千多年之前,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,艺术情怀的弘广。回去罢,时间已经不早。怕还要下雪。1.文中不止一次写到“雪”,写 “雪”有什么作用?
3、(三)《行吟阁遐想》黄秋耘前几天,翻出一张旧照片,是我自己拍的武昌东湖旁边的行吟阁。这张已经开始有点褪色的照片,引起了我一段深沉的回忆。五年前的初春,我因事去广州,路过武汉。在一个大雪后的晴天,我前去东湖,在行吟阁和屈原纪念馆一带盘桓了大半天。不知道为什么,对于屈原,我有一种“旷百世而相感”的特别感情。从少年时代起,我就爱读《离骚》,每读到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、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时候,总是“唏嘘而不可禁”。不过,我真正理解屈原的精神和《离骚》的真谛,还是在直接受到闻一多先生的教诲以后。说起来,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,闻一多先生主讲的《楚辞》是我最喜欢的功课之一。闻先生上课是不拘形式的,别的教师都在日间上课,他偏偏把课程排到晚间。我还记得,每当华灯初上,或者皓月当头,他总是带着微醺的感情,步入教室,口里高吟着:“士无事,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方可为真名士!”接着,他就边朗诵,边讲解,边发挥。时而悲歌慷慨,热泪纵横;时而酣畅淋漓,击节赞赏。与其说闻先生是以渊博学识、翔实的考证、独到的见解吸引着我们,毋宁说他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、深沉的悲悯情怀感动着我们。1935至1936年间,敌人的铁蹄已经越过了长城。那时候,几千里锦绣河山,几十座繁荣城市,都已经遭受践踏。旧时在那些暂时还没有沦陷的国土上,南瞻北望,又何处不是哀鸿遍野,民不聊生?这艰难的岁月跟屈原的时代是多么相像啊!因此,闻先生的孤愤高吟、长歌当哭,就更容易引发我们的共鸣同感了。有时候,我甚至感觉到:在闻先生的灵魂里就活着一个屈原,他好像就是屈原的化身。且说我那天来到了行吟阁畔,东湖两岸,积雪茫茫,素裹红装,江山如画,四顾无人,万籁俱寂,连几里外水鸟振翅的声音都听得到。我参观过屈原纪念馆之后,又在矗立湖滨的屈原像前凭吊一番。我仿佛看到这位项上挂着花环、腰间佩着长剑、足下穿着芒鞋的古代诗人,披发伫立,蹙额低吟:“瞻前而顾后兮,相观民之计极。夫孰非义而可用兮,孰非善而可服!”我又仿佛看到穿着破旧的长袍、飘拂着长髯、背着双手的闻一多先生,昂首仰天,血脉偾张,作狮子吼:“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,有一句话能点着火,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,你猜想透火山的缄默?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,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,爆一声:咱们的中国!”后来这两个形象就合而为一,何者是屈原,何者为闻先生,我都分不清楚了。我无意以古人喻后人,以后人比古人,但一接触到与屈原有关的事物,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闻一多先生的风貌。的确,他们虽然相隔两千多年,但无论是对人民的热爱,对祖国的忠贞,还是斗志的坚强,死事的壮烈,都是颇有些相似的。因此,漫游之余,我又忽生遐想:闻先生是湖北人,且曾几度寓居武昌,假如在行吟阁上,屈原馆中,另辟一室,陈列先生的衣冠遗物、著作手稿以及金石创作,使这古今两位伟大的受国诗人相得益彰,也许不见得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吧。作为一个景仰闻一多先生的学生,我是殷切地期望着的。2.屈原与闻一多的形象在作者心目中“合而为一”,原因是什么?